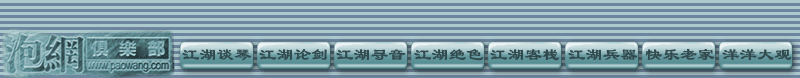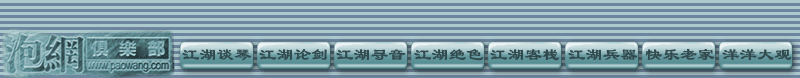|
|
|
| 北岛的北京
|
| 时间:2010/10/26 出处:朱涛 |
北岛的北京
——读《城门开》手记
朱涛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飘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北岛《序:我的北京》
二〇〇一年底,诗人北岛得到一次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他赫然发现那城市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从那时起,北岛开始酝酿一项重建工程。他要用文字重建这个城市,恢复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想象的北京。经过几年的写作,这项工程终于竣工,交付使用了——这就是今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出版的《城门开》。
我本人是在八月的香港书展中, “第一时间”抢购到这本书的。在随后的十几天中,我带着它去上海度假,看世博。每天白天,我在上海百年不遇的酷暑中,经受各种光怪陆离的世博场馆的视觉轰炸。到了晚上,我一个人静下来,叩开北岛的城门,进入另一个世界。
该书不是一部严格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完整”的回忆录,而是由一系列主题性叙事片段组成的散文集。每篇散文既都可独立成章,像一座座独立的四合院,又相互勾连、重叠,汇成一整座城池。我在初读时,感觉各篇散文的片段感很强。进入其中任一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生动的细节描述。从一篇踱步到另一篇,则有一种步移景异的游园般感受。读完一遍后,拉开焦距整体观察,犹如逛完紫禁城,爬到景山向下俯瞰。我发现,作者其实颇为精心地规划了整本书(城)的结构。这里为方便起见,我姑且总结为起、承、转、合四部分。
起:感官之城
(《光与影》、《味儿》、《声音》)
城门一打开,北岛首先将游客引入三种与个人感官紧密相连的北京记忆:“光与影”——视觉记忆的北京,“味儿”——嗅觉和味觉记忆的北京,“声音”——听觉记忆的北京。通过这三座感官之城,北岛展示出他独特的“城市现象学”:他的北京,与那些旅游画册和明信片上反复宣传的,几近陈词滥调的“官方图像”完全无关,而与他非常个人化、具体的细节记忆和感受紧密相连。更进一步,为帮助游客们充分“张开”感官,北岛还特地强化了各种效果描绘,就像我们为了让图像更醒目,在软件Photoshop中滑动阀门,加大图片的色彩饱和度、明暗对比度和变形程度一样。
在《光与影》中,北岛写到他儿时北京的夜晚之暗。与现在晚上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 的北京相比,那时的北京之夜“至少暗一百倍”。不同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宏大概念框架中来表达他的“阴翳礼赞”,北岛对北京之暗的回忆不加任何抽象的概念诠释。他的笔触始终紧贴在对个人感觉的描述上——在黑暗中,人的视力变得超强,女孩们都“显得”很好看,孩子们可以尽情捉迷藏,可以恐惧而又兴奋地想象着鬼的浮现,等等。与谷崎多少有些观念重叠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夺目的夜晚灯光照明,显然与城市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现代化”有关。北岛在文中也和我们分享他儿时初见“现代性之光”的喜悦。那时刻,北京之夜的魅力在于局部的光明与其它大片幽暗的城市空间之间的戏剧性对比: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在《味儿》中,北岛说关于北京,首先让他想到的是随季节变化的各种气味儿。换句话说,人,有点像狗,对城市、空间的最深刻感知,并不在视觉上,而是在嗅觉和味觉上。北岛这八页文字,弥漫开的首先是各种嗅觉的(气)味儿——儿时北岛“嗅”出的北京城市空间:冬天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灰尘味儿和大雪的云中薄荷味儿、春天令人昏睡的杏花梨花水仙花香、夏天游泳池中的福尔马林加漂白粉混合着尿骚味儿、秋天浸泡在雨水中的树叶霉烂味儿等等。然后是各种味觉的味(道)儿——儿时北岛(偷)吃出的北京记忆:鱼肝油味儿、“大白兔”奶糖味儿、味精味儿、桂皮味儿、臭豆腐味儿等等。
在《声音》中,北岛“绘声绘色”地写了他小时候各种人声、动物声、器械声交汇成的声环境。我尤其喜欢少年鼓手赵振开(北岛本名)那一段,展示出北岛在声音和图像之间制造“通感”的高超技巧。理想中军乐队鼓手的鼓点应是“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这里,“骏马”是一个多么革命浪漫主义的意象!而现实中的少年赵振开苦练几个礼拜,敲出的鼓点却不过是两头瘸驴。它们先是各自拉磨,然后磕磕碰碰的离开磨盘。最后虽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总达不到奔马的境界。在正式队列仪式那天,鼓手赵振开紧张得心跳如鼓,上台时腰间小鼓不慎怦然落地,惹得全场大笑——一个鼓手的命运就这样滑稽地结束。紧接下来,北岛笔锋一跃到六十年代中期,音频骤然加高、音速加快,纺织机的噪音和高音喇叭中的革命口号充斥在空气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在该文的最后一段,少年鼓手鼓点中那小跑的毛驴魔幻般地重现了。这次不再是两头,而是一群,亡命地出现在革命的初夜:
文革初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很多人在写回忆时,往往以一种尘埃落定,心气儿早过的心态,不自觉将过去的一切都罩上一层浪漫感伤和怀旧的柔光。这些回忆通常以两种方式收尾:要么是空泛的赞叹——啊,青春万岁!要么是无谓的感伤:时光如梭,无可奈何花落去 ……但北岛总是坚定地拒斥这种毫无批判性的情感“放松”。在以三篇的篇幅,如此细腻地描绘了儿时北京的各种感官细节后,北岛几乎残酷地将读者对情感浪漫升华的心理期待陡然悬置在一片凌乱的驴蹄声中。这十几头毛驴,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大革命时代中的“山寨版”骏马。它们在厄运当头时,显然达不到“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境界,也没有“马群踏弯空气”(柏桦)的将暴力唯美化的情操。但是不管怎样,它们仍在可怜巴巴地努力:“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这结尾突现出北岛文字内含的巨大张力。这张力贯穿全书每个篇章,它是在调度各种紧张的冲突中产生:克制的文字与纷乱的叙事之间的矛盾,前景中各种精致、微妙和闪光的细节与背景中袭来的大片不祥阴云之间的反差,诸多角色的先天卑微和缺陷与其后天努力挣扎之间的不协调,一个全身心沉浸在童年快乐和哀伤中的灿烂的小北岛与另一个抽离出来,痛苦反思的冷峻的老北岛之间的对峙,等等。所有这些冲突都透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美和荒谬感,让读者既陶醉其中,又感到心理不得安宁。
承:玩物之城
(《玩具与游戏》、《家具》、《唱片》、《钓鱼》、《游泳》、《养兔子》)
这部分集中回忆北岛童年少年的玩耍,以及接触到的各种物件和动物。在对儿童玩耍的生动描绘上,这组散文让我想起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两者有重大不同:鲁迅笔下的儿童游戏是对枯燥书塾生活的反叛,是孩童们“真善美”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北岛笔下,儿童游戏本身是复杂的。貌似纯洁的游戏,时时会从内部泛出一些晦暗之色。这暗色要么体现为儿童在游戏中所体验到的无能或挫败感,要么来源于成人冷酷世界对孩童世界的渗透和侵蚀,要么直接反映出孩子们 “天生的恶意”——也许那就是人性之恶。
《养兔子》讲的是北岛在五十年代末,自己“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时养宠物的故事。继小鸡和蚕死于非命后,小北岛养了一对饭量惊人的兔子,日益挑战本已相当贫瘠的食物资源,让雄踞地球食物链最高端的人深感不安。终于一天,北岛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父亲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小北岛一大早就躲出去——“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这里作者没有费一点笔墨直接书写小北岛的心情,但一系列空间穿梭和最后的迷失已经把他的失魂落魄表达得活灵活现。更妙的是,下面作者的镜头蓦地一转,让我们从迷失的小北岛眼中,看到一幅玛格丽特式的超现实画面:
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态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如果说“通感”构成了前部分“感官之城”的灵魂,那么“通灵”则赋予这部分“玩物之城”中万物以魔力。比如,在《唱片》中,几张稀有的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忽而伴随知青到内蒙,忽而在北京召集起文艺沙龙,忽而引发不同沙龙间的血腥殴斗。在《家具》中,一堆家具不单单消极地反映主人物质生活和审美诉求的变迁,也和主人一样个个有生老病死,似乎也有七情六欲。
《玩具与游戏》是这部分份量最重的一篇,读来让我觉得既好玩,又心中发怵,有时甚至感到有戈尔丁的《蝇王》和哈内克的电影《白丝带》般的阴影袭来。北岛先提到他最早的玩具铁皮汽艇和玻璃汽车,他每逢寒假与他五舅家四千金一起玩的小女孩游戏如染指甲、跳皮筋等,还有他与男孩儿们常玩的斗蛐蛐、“扇三角”、弹玻璃球、抽陀螺、滚铁环等游戏。然后他着重写了男孩游戏中的“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他和玩伴们对武器的热爱,对玩飞刀、放鞭炮和打仗的热衷。他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九年春节下午,两拨男孩儿,依靠假山和楼门口形成攻守之势,利用弹弓、鞭炮和簸箕为攻守武器,发动了一场战役 ——“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
正当那个阳光灿烂的小北岛在撅着屁股,忙着玩打仗时,目光冷峻的老北岛紧接着在下一段——全文的最后一段走出来了。在老北岛眼中,小北岛(们)沉浸其中的游戏,不过就是对他们即将进入的残酷成人游戏的一种模拟或彩排罢了。以他特有的悲天悯人,北岛这样结束全文: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刀实枪的战争。文化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转:人与事
(《三不老胡同一号》、《钱阿姨》、《读书》、《去上海》、《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
前述两部分的文字多聚焦在对记忆中的空间、景物、东西和活动的描绘上,人物往往成为烘托空间的“配景人”。从这部分起,作者叙述的图底关系反转了:城市、空间和景物隐为模糊的背景,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跃到前景,成为叙述的焦点。一些人物,如“钱阿姨”,曾在前面不同场合中闪现过几次,仿佛环环相套的庭院迷宫中晃过的人影,到这部分被聚焦,集中叙述。
在空间版图上,这组散文组成一个放射状结构。中心点是北岛自八岁起一直住在里面,长达二十多年的“三不老胡同一号”(北岛家在四楼443号)。这是一栋外面弥漫着烤白薯味道,从四楼阳台可俯瞰北京的排浪般四合院瓦顶的红砖楼房。围绕着这个根据地,各种人与事得以紧密交织,或偶尔放射出去——包括北岛的小学、中学经历,八岁时第一次远行去上海,十七岁时首次离开父母,“大串联”到西部和南方,最后回到北京。
一九五八年,三不老胡同一号大院中办起食堂、架起小高炉炼钢,狂打麻雀。接下来是饥饿、浮肿和作者终生难忘的几次打牙祭。文革爆发了,正如北岛前面《玩具与游戏》中写的,孩子们“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作者本人,昔日那个努力想敲出“骏马奔驰”的少年鼓手,那个幻想能在泳池跳台上潇洒一跃吸引无数女孩目光的男孩,那个已在各种打仗游戏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士,十七岁了。他成了孩子王——一个小“蝇王”,带领五六个男孩,去揪斗大院里的一位“历史反革命”。北岛对揪斗过程的描绘细致、冷静,但读起来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现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揭露和责怪别人的“过错”,相对来说容易些。但要回顾自己的作为,揭开个人内心的黑暗,以自我为标本剖析人性之恶,无疑是艰难、痛苦的。这既需要理性批判的勇气,也需要手术刀般锐利、精确和无情的文笔。以下是北岛对他自己亲自动手,给那个“反革命”剃“阴阳头”的描述: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四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晕旋,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到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的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谁也不会想到,这少年们起初以为刺激好玩的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一号大院内开始有人自缢,被抄家,被殴打,被遣送回原籍,被送去插队、参军、劳改等等。到六十年代末,三不老胡同一号几乎人去楼空。到一九六九年春,北岛随单位迁到北京房山,得以两周大休回家一次,三不老胡同一号的家成了他和一帮文艺青年朋友的聚会场所。到一九七八年底,北岛和朋友们创办了《今天》,部分装订工作在那里进行。家里满地都是油印纸,门庭若市。直到一九八〇年,北岛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一号。
《读书》讲儿时北岛在各种小人书和阁楼“禁书”中的精神游历,《去上海》则回忆他在八岁时(一九五七年)的首次城际旅行。与北京相比,上海是另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上海提供了一个空间参照系,使得北岛首次拉开距离,重新辨认他的故乡,得以量出北京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
在《序:我的北京》中,北岛写道: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种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我认为不妨对北岛这段回顾人生的文字做一种空间的读解:童年青少年时的空间环境——北京城对北岛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他的一切远行,都是他的北京的向外延展。或换句话说,长大后“满世界近乎疯狂的奔走”的北岛,实际上是在朝着各种方向,试图企及对他儿时北京的回归。
接下来的几篇,《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显然是按作者的成长历程一字排列。读起来让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加速度贯穿其间:时间在加速,空间在急剧扩张和重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强。在这部分,《北京四中》在篇幅、时空跨度和强度上,可说是与前面《三不老胡同一号》相对称的一篇。相对而言,《三不老胡同一号》像一出话剧,在较为稳定的空间平台上,一幕幕地上演各家庭、人物在时代冲击下的聚散离合;而《北京四中》则更像一部电影。虽然绝大部分故事都集中在一个空间环境——中学校园里,作者的叙事也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但是由于作者的叙述节奏越来越快,事件更替越来越让人目不暇接,人与人、代与代、阶层与阶层、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碰撞越来越“白热化”,全篇读完后,我居然有一种看了一部充满蒙太奇剪切、时空倒错的电影的感觉。
在这部“电影”中,充当配角的是几位老师和工作人员。他们在出场时个个生龙活虎,但很快到了文革,或被批斗,被学生拳打脚踢,或跳河、割喉自尽,匆忙退场。担任主角的是北岛和他的同学们。他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他们当时的天真胡闹、真诚探索,以及残酷的派系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今日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基础。
北京四中的批斗会(1960年代)
北岛回忆道,一九六五年,十七岁的他初进校园时的感受: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第二年,文革爆发了。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带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贫民学校。这种内在分裂起初被刻意掩盖起来,在文革中被“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学生们按不同出身和家庭背景分化成不同派系组织,学校很快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学生派别中有带有先天出身优越感,自认为掌握权力和国家未来的“四四派”(“老兵”),也有提倡“打碎特权阶层”,“实行财产再分配”的“四三派”。两派不但通过大字报和自办报纸进行思想论战,还在四中校园里展开血腥的武斗。在最后,“文革”草率收场时:
在两派冲突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写到这里,冷峻的老北岛再次出场,痛切地反思: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北岛和同学一起摄于天坛(1968年底)
北京四中是北岛人生的转折点。他和他那一代人,匆匆告别耽于幻想的儿童世界,投入到充满争斗的成人现实。这剧变制造出多重历史悲剧。其中一重是:反观二十年后,甚至四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现状,或许真的证明当年那些“老兵”是确有“远见”的。另一重悲剧更在于:很多和北岛同龄的热血青年甚至都没机会等到二十年后,他们的生命就早早陨落了。例如著名的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于一九六八年被捕,于一九七〇年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高二二班的学生张育海,为躲避工宣队的审查,先逃到云南农场,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于一九六九年在战斗中身亡,年仅二十一岁。在死前没几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合:父亲
北岛的父亲曾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写书或造城也是个“接送”。在以感官开启城市,以玩物承接城市,以人与事铺展开城市后,北岛最终要用一篇文章,合拢和告别整项工程——他的北京重建和他的心路历程。他选择了以“父亲”结尾。
这一定是整本书写作中最艰难的一篇,因为作者要同时与至少三重意义上的“父亲”对话、和解和告别——与和作者充满感情纠葛和观念冲突的父亲本人,与父亲所经历的时代,与父亲所代表的那个深远的父权文化传统。我从本篇中急促的叙述节奏,剧烈的时空穿插,多重甚至可说是纷乱的思想线索,大量欲言又止的段落,以及戛然而止的结尾,都能感受到作者痛苦的灵魂挣扎。
起初,当父亲还不是“父亲”时,也经历过“儿子”所经历的灿烂的青春岁月。北岛选取了父亲一张“充满青春的自信”的照片,作为对他回忆的起点。在作者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很有耐心,总陪他和弟弟妹妹玩。与父亲开始发生冲突是在作者七岁左右。在保险公司宿舍中,与作者家合住一套单元的另一家主人俞彪文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似乎风暴紧跟着也钻进作者家门缝儿,家中气氛变了:
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量。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自搬到三不老胡同一号后,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
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不光成为家庭中无可挑战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权力也从家中向外延伸。比如,他代表组织找“犯错误”的门邻谈话。他任民进中央副宣传部长时,定期拜访当时挂名宣传部长的谢冰心,饮茶清谈,然后向组织汇报谈话内容,以协助组织对谢冰心进行“思想改造”。后一件事是父亲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向北岛提起。吃惊的北岛劝父亲把一切写出来,对自己和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个交代。父亲答应“再好好想想”,但就此搁置下来。直到北岛今天在《父亲》这篇散文中,算是履行了当时父子达成的默契:“说出真相,不管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一九七二年,北岛和他一帮“先锋派”朋友在家中的频繁聚会和他们展示的作品,开始严重挑战父亲的权威性和安全感。当北岛给父亲看他的《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父亲被“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这样的句子所惊骇,责令北岛马上将诗稿烧掉。北岛的朋友彭刚以赭灰色的基调和表现主义手法临摹的列维坦的油画《湖》,挂在北岛的床铺上方,触发了另一场父子冲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
北岛就真的“滚出去”,在外面晃悠一段日子。每次要靠母亲出面调停,才能把游子劝回家。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人生真是“环环相扣”!北岛这个“逆子”,从三十多年前被一次次逐出家门,直到二十多年前被逐出国门——这时再没一个调停的“母亲”,他可能今生无法再“回家”——是不是正是这高昂的人生代价,才驱使今天的北岛宁愿忍受痛苦,也要追问“父-子”问题,探究“父亲”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角色?北岛似乎逐渐看清了一个骇人的场景:正是一个超尺度的“父亲”角色,从端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中央的君王,到无数个端坐在四合院堂屋里的“家庭最高行政长官”,贯穿着“国-家”所有权力层次和单元,组织起一个无边无际,但又高度一体化的空间迷宫——一如成龙在国庆献礼歌曲《国家》中深情地唱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更可怕的是,北岛发现,这“国-家”迷宫是四维的——它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繁衍。不管“后代”多么离经叛道,不管“后人”的城市和居住空间格局发生多大的变化, “君王-父亲”这个角色始终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代、每一个中国男人——包括他自己——的心中: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文开头,北岛引用了他《给父亲》的诗句: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当然,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不管其中有多强的政治意味,本质上仍是以家人亲情为基础的。除了解剖“父亲-父权”问题外,北岛还在文中花大量篇幅描绘他父亲的各种生活细节,如他对家族历史的探究,口味驳杂的读书爱好,对技术的痴迷——从组装半导体和黑白电视机,到对新时代音响、摄像机和电脑的迷恋,等等。看得出来,在父亲晚年,北岛——本身也已成为父亲——特别渴望与父亲交流,在爱中得到和解。但是,也许 “辈份”的隔阂实在无法跨越,也许历史在双方的记忆、经验中留下太多的晦暗点没法澄清,也许我们的现代汉语本身就缺乏父子交流的语言,北岛的愿望无法实现:
自80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这困境,也影射着今天的我们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种种纠葛与无奈。而父亲本人似乎早早就参悟了:“人生就是个接送”。不管肚里憋着多少话还没说出来,不管脑海里还埋藏着多少往事没理清,没给后人交代,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得走。在写那个最终时刻之前,北岛以倒叙的手法插入两段闪回——他父亲自己关于“存在与虚无”的评论。第一段是近期发生的:
一九九九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第二段一下子回溯到一九五八年。这一段显然也是对全文开头那个“充满青春的自信”的父亲的呼应,只不过这里的父亲,更带有一点虚无的气质: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那一刻终于到了。二〇〇三年元月,北岛第三次获准回北京,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即将去世,儿子也不得不远离故乡。这是永久的告别:
……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他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这就是本篇《父亲》和全书的结尾。
一百多年前,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宣判:“这个杀掉那个”——建筑曾是记录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但是自印刷术发明后,书本作为更强大的“媒体”取而代之——“书本杀掉建筑”。今天的北岛,远没有当年雨果那种对文学伟力的过度信赖。他更像一个目送文明逝去的守夜人。他悲切地发现:根本不是书本,或任一种单一的“新媒体”,杀掉建筑或城市。是全方位的、暴风骤雨般的“历史进步”,在短短几十年间毁掉了他童年青少年的北京城,在物质、空间层面上将关于北京的感官、玩物和人与事的记忆悉数抹除。而今唯有书本,唯有语言,才能起到一点微薄的记录和凭吊作用,或许还能帮助唤醒一些后人对历史记忆和生存环境的感知。就在这“默默祈祷”中,北岛合拢了他的《城门开》。
2010年8-9月上海-香港
(本文经删改后,发表于《上海书评》2010年10月17日) |
|